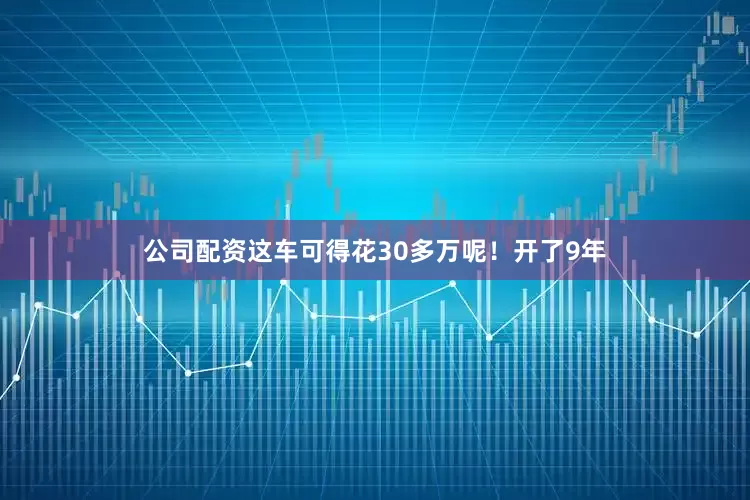驻村贺窑的第二个秋天,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。清晨的薄雾漫过村西黄丘山套的余脉,我坐在村部窗前,再次翻开申报山东省革命老区村的材料。指尖抚过纸上“贺明谟、王兆汉、贺敬宜、赵德全、韩成信”五个名字,纸页间仿佛还留着岁月的温度,一份沉甸甸的敬仰从心底漫上来。
初到贺窑村时,老支书老孙就拉着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讲过往。“咱这地儿,西临运河支队根据地,当年可是共产党在峄南的‘桥头堡’。”他往远处连绵的山影一指,语气里带着骄傲,“鬼子、汉奸来了多少次,炮火把屋顶掀了,刺刀把墙戳穿了,愣是没把这村子的骨头压弯。”
村头烈士纪念碑上,贺明谟的名字刻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村里72岁的贺大爷总说,这是咱村的“硬汉子”。1940年“巨桥惨案”那回,他带着村民帮运河支队藏弹药、探敌情,被日军围捕后绑在老槐树上。敌人用枪托砸、用凉水灌,他咬紧牙关只说一句话:“要杀便杀,想从嘴里掏东西,没门!”最后和其他27名志士一起倒在血泊里,那年他才28岁,家里的娃刚满周岁。去年冬天,贺大爷颤巍巍地从木匣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,相纸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褂子,眼神亮得像星子。
展开剩余60%王兆汉的故事,老孙每次讲都红着眼眶。他是村里的农救会会长,白天带着乡亲们种粮,夜里就摸黑给部队送情报。汉奸“龙瓜屋子”恨他入骨,趁夜把他堵在自家柴房里。烙铁烫在身上滋滋冒烟,刺刀架在脖子上寒光闪闪,他到死都梗着脖子骂:“老子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,要杀要剐随便!”老人们说,他牺牲那天,村东头那棵几百年的老槐树,不知怎的落了一地叶子,像铺了层厚厚的泪。
贺敬宜、赵德全、韩成信这三位烈士的故事,藏在申报材料的字里行间。档案里记着,贺敬宜在解放台儿庄的巷战中,抱着炸药包冲进敌人碉堡;赵德全为了掩护乡亲转移,把敌人引向悬崖;韩成信用自家的油灯给地下党开会议事,最后在传递情报时被特务杀害。
驻村这两年,我利用寒暑假期间开设红色文化快乐营,给他们讲这些故事。有次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贺敬宜的名字问:“书记叔叔,他和写《回延安》的贺敬之是亲戚吗?”我笑着点头:“咱贺窑人有血性,不管是扛枪的还是握笔的,心里都装着家国。你看这村子,既是孕育英雄烈士的地方,也是走出文臣武将的热土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,却把“英雄”两个字牢牢记在心里。
站在秋阳里,望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通向山外,再回望五位英烈,忽然懂了:先烈们用生命护下的,从来不止这方土地,更是“活下去、活得好”的希望。
作为驻村书记,我能做的,就是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成他们当年期盼的模样。让红土地上长出金色的麦穗,让孩子们的笑声盖过当年的枪炮声,让这方浸透鲜血的土地,结出更丰饶的果实——这,大概就是对“铭记历史、开创未来”最实在的注解。(通讯员:贾继伟)
发布于:河北省股票配资排名在线查询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